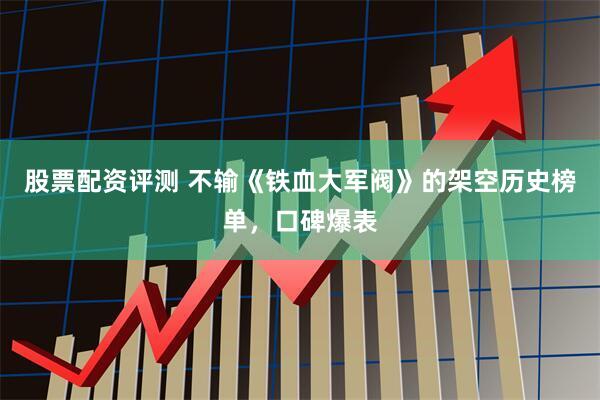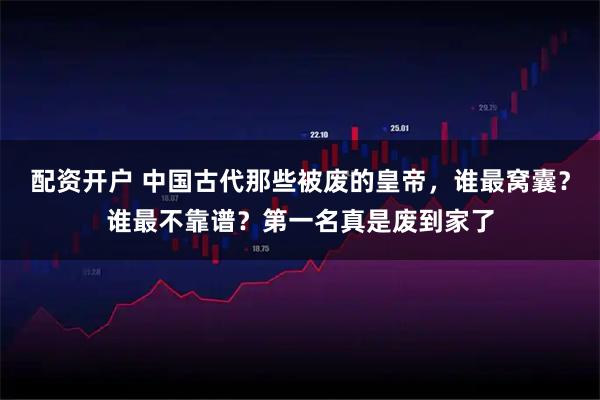
在中国漫长帝制史的高墙深院之中配资开户,被正式废黜的皇帝寥寥无几。
不是因为没人想动龙椅,而是废帝牵涉天命、礼法、宗庙、人心,动辄引发朝野震荡,甚至政权崩解。
故而,除非局势逼至绝境,或君主自身彻底失控,否则废立之举,鲜有敢行者。
但一旦真有人被拽下皇座,其背后往往不是单一的道德败坏,而是权力结构撕裂、政治秩序失衡与制度性危机的集中爆发。
刘贺便是这样一个突兀又典型的案例。
他于昭帝驾崩后被迎立入京,名义上是继统大统,实则是大司马霍光为维持自身掌控力而选定的过渡人物。
霍光需要的不是一个有主见的君主,而是一个能默许其继续摄政的符号。
偏偏刘贺全然未察此局,以为登基即意味着权力到手,迫不及待地将昌邑旧部尽数迁入长安,大肆封授,连奶母都引入宫中参预机务。
这种行为在汉代礼制与政治惯例中几近僭越。
尤其在国丧未除之际,于未央宫内奏乐宴饮,更是对先帝与宗庙礼法的公然践踏。
更致命的是,他试图更换长乐宫卫尉。
长乐宫乃太后居所,亦为宫廷防御关键节点,卫尉人选向来由霍光亲自掌控。

此举动摇霍氏兵权根基,形同宣战。
霍光随即召集丞相、御史、诸卿及列侯共议废立。
会议仅用一日便达成一致,随即率兵入宫,宣读太后诏书,历数刘贺“行昏乱,危社稷”之罪,当场收玺绶。
整个过程迅疾而有序,显示出霍氏集团对中枢的绝对控制力。
刘贺被废后,史称“汉废帝”,昌邑国除,贬为海昏侯,二十七日帝王生涯就此终结。
他不是死于阴谋,而是死于对政治现实的彻底误判——以为龙袍加身即能号令天下,却不知皇权早已被权臣架空,自己不过是他人棋盘上一颗可弃之子。
刘贺的荒唐事,《汉书》载其“受玺以来二十七日,使者旁午,持节诏诸官署征发,凡一千一百二十七事”。
此数字虽可能为修史者夸张,但其行为密集、违制、越礼之频繁,足以证明其毫无帝王素养。
他既无政治敏感,亦无制度敬畏,更无对霍光真实意图的洞察。
他被废,是制度对失控君主的自动清除,亦是西汉中期外戚与皇权博弈中一次精准的外科手术。
若说刘贺是自毁于无知,那李重茂则根本连“自毁”的机会都没有。
他生在神龙政变之后的唐朝,一个皇权被后妃、公主、宦官与宗室反复撕扯的时代。

其父中宗复辟后,韦后与安乐公主干政日甚,朝纲渐弛。
中宗暴卒,死因蹊跷,《旧唐书》《资治通鉴》皆暗示韦氏下毒,意在效法武则天临朝称制。
为稳住局面,韦后集团与太平公主、上官婉儿等势力短暂妥协,共同拥立年幼且母族卑微的李重茂为帝。
李重茂登基时年仅十六岁,既无母族外戚支撑,亦无军功根基,更无政治班底。
他的存在,仅是为了在过渡期内维系李唐国号的合法性。
韦后称“皇太后”,临朝摄政,安乐公主则求为“皇太女”,意图接班。
这种安排早已触碰李唐宗室与关陇贵族的根本利益。
被贬在外的临淄王李隆基,迅速与太平公主密谋,集结禁军万骑,发动唐隆政委。
政变当夜,羽林军突入宫中,斩韦后、安乐公主及其党羽。
次日,李隆基率兵入宫,太平公主亲自上前,对李重茂说:“天下之心已归相王(李旦),此非儿座。”
随即命左右扶下御座。
李重茂未发一言,未行一令,甚至未被允许正式退位诏书。

他被废为温王,后改封襄王,不久便死于贬所,年仅二十岁左右。
李重茂的“帝位”从一开始就是伪命题。
他没有被当作君主对待,而是当作一件可随时更换的礼器。
他的废黜不涉及任何政治过失,纯粹是权力重组中的清理环节。
在那个时代,皇位已非神圣不可侵犯,而成了各方势力角力的战利品。
李重茂的悲剧在于,他连成为棋手的资格都没有,只是棋盘上被随意移动的卒子,一旦无用,即刻弃之。
再往后看东晋,司马奕的遭遇,则揭示了另一种废帝逻辑——无需实罪,只需借口。
东晋自衣冠南渡后,皇权式微,门阀与军阀轮番掌权。
桓温凭借平定蜀地、三次北伐之功,早已凌驾于朝廷之上。
晋哀帝死后,其弟司马奕被立为帝。
此人史载“谨愿”,无显著劣迹,亦无重大建树,正符合桓温对傀儡君主的要求。
但问题在于,桓温野心不止于权臣,他欲效仿伊尹、霍光,更进一步,行禅让之事。

然而司马奕在位六年,并未犯下可被公开声讨的大过。
桓温无法以“昏聩”“暴虐”为由废帝,只好另寻他法。
他指使其心腹散布流言,称司马奕阳痿不育,且宠信嬖幸,致宫中无嗣。
此说虽无实证,但在重视宗庙继承的礼法社会中,足以动摇君主合法性。
桓温遂以“宗庙社稷将绝”为由,奏请褚太后下诏废帝。
诏书称:“奕不能承天序,奉宗庙,宜废为海西县公。”
整个过程干净利落,毫无波澜。
朝臣无人敢抗,宗室无人敢言。
司马奕被废后,居于吴县,终日闭门不出,唯恐遭害。
他死后,朝廷仅以公礼葬之,未复帝号。
他的存在,从登基起就是权臣为自身篡位铺路的工具;他的废黜,则是权臣在找不到合法理由时,硬造一个“合法”借口的典型操作。
在东晋,皇权已彻底沦为军阀野心的装饰品,废立不过是一纸文书之易。

至于建文帝朱允炆,他的下台则是一场家族内战的必然结果。
洪武三十一年,太祖朱元璋崩,遗命孙允炆继位。
此举虽合礼法(嫡长子已故,嫡长孙承统),却埋下巨大隐患——诸藩王,尤其是燕王朱棣,手握重兵,镇守北边,地位尊崇,岂甘屈居少年新君之下?
朱允炆登基后,采纳齐泰、黄子澄之策,推行削藩。
其初衷无可厚非:藩王拥兵自重,威胁中央集权,自汉七国之乱、晋八王之乱以来,历代皆以为戒。
但建文君臣的执行策略却严重失误。
他们先削周、齐、湘、代、岷诸王,或废为庶人,或幽禁致死,手段激烈而缺乏缓冲。
诸王或无兵可抗,或孤立无援,故迅速平定。
唯独对燕王朱棣,既忌惮其兵强,又犹豫不决,未在初期果断处置,反使其获得喘息与准备之机。
朱棣起兵时,打出“清君侧,靖国难”旗号,指斥齐泰、黄子澄为奸臣,宣称只诛此二人,不反天子。
此举巧妙利用了儒家“君为社稷,臣为君”的伦理框架,将叛乱包装为忠君之举。

加之建文朝廷用人不当,屡换将帅,战略摇摆,士气低落。
耿炳文守而不攻,李景隆大败于白沟河,盛庸、平安虽有小胜,终难挽全局。
更致命的是,随着战事胶着,越来越多的北方将领与地方势力倒向朱棣,视其为能结束内乱的强主。
建文四年六月,燕军渡江,直逼京师。
谷王橞与李景隆开金川门迎降,南京陷落。
宫中大火,允炆下落不明。
官方记载称其“阖宫自焚”,但民间多传其易服出逃,流落西南或闽浙,甚至有说其出家为僧。
无论真相如何,其皇位至此终结。
朱棣登基,是为成祖,旋即革除建文年号,复称洪武三十五年,意在抹去建文一朝合法性。
朱允炆的失败,不在其心志,而在其经验与手腕。
他生于深宫,长于妇人之手,虽受儒学熏陶,却无实际治军理政之能。
他信任的文臣多为理想主义者,缺乏权谋与应变之术。

削藩本为巩固皇权,却因操之过急、判之不明,反激成大祸。
他不是被外敌所废,而是被叔父以武力夺位,其“废”是成王败寇的直接结果,亦是明代皇权继承制度内在矛盾的一次血腥爆发。
回看这四人,刘贺之废,咎由自取;李重茂之废,身不由己;司马奕之废,莫须有罪;朱允炆之废,兵败国亡。
他们共同勾勒出帝制时代“废帝”现象的多重面相:或因君主失德,或因权臣专横,或因宗室相残,或因制度缺陷。
废帝从来不是简单的道德审判,而是政治系统在极端压力下的自我调整机制——当君主无法履行其象征与实际功能时,便会被体制无情抛弃。
刘贺的昌邑旧臣被尽数诛杀,仅王吉、龚遂因屡谏得免。
这说明霍光废帝并非仅针对个人,更是对一股潜在政治势力的清洗。
李重茂被废后,李隆基与太平公主共掌朝政,不久即因权力冲突再度爆发政变,太平公主被赐死,玄宗独揽大权。
这证明废帝只是权力过渡的中间环节,真正较量在废立之后。
司马奕被废,桓温虽未如愿称帝,却为日后桓玄篡位埋下伏笔。
东晋皇权自此再无复兴可能。
建文帝一系被彻底抹去,直至万历年间方有臣子奏请恢复建文年号,迟来的平反,难掩当初的血腥。

这些被废之帝,有的留下墓葬,如近年发掘的海昏侯墓,出土金器、简牍、车马,印证其短暂富贵与仓皇结局;有的仅存史书寥寥数语,如李重茂,连生卒年都模糊不清;有的成为谜团,如建文帝,数百年来野史笔记纷纭,竟成文化母题。
他们的命运,被不同时代的权力逻辑所切割、重塑、遗忘或重述。
废帝事件的发生频次,在整个帝制史中极低。
两汉四百余年,仅刘贺、刘辩二人被正式废黜;唐代近三百年,李重茂之外,另有中宗一度被武则天废为庐陵王,但属女性称帝特殊背景;宋代无废帝;元代有天顺帝被元文宗废杀;明代仅建文帝;清代无。
可见,废帝始终是极端情况下的极端手段,非到万不得已,无人敢动。
礼法体系为皇权提供了神圣性,但也为废帝预留了通道。
《尚书》有“天命靡常”,《孟子》言“闻诛一夫纣矣,未闻弑君也”,皆为废黜暴君提供理论依据。
但实际操作中,废帝极少以“暴虐”为由,更多是“失德”“无子”“幼弱”“权臣操控”等模糊理由。
这说明,废帝的核心动力从来不是道德,而是权力再分配的现实需求。
霍光废刘贺,需借太后名义,走程序正义;桓温废司马奕,亦需褚太后下诏;李隆基废李重茂,由太平公主出面宣布;朱棣夺位,则需制造建文自焚假象,再以“继统”姿态登基。
他们都在极力维持礼法外表,哪怕内里早已赤裸裸是武力与阴谋。
这恰恰证明,即便在皇权最虚弱的时代,礼法这张皮仍不可撕破——一旦撕破,便是天下大乱,无人可制。

被废之帝的命运,往往比亡国之君更惨。
亡国之君尚可得敌国礼遇,如隋恭帝、陈后主;废帝则常被圈禁、监视、甚至暗杀。
司马奕居吴县,每有使者至,便“惶怖”,以为将被赐死;刘贺虽封侯,亦被严密监视,不得参与政事;李重茂早夭,疑为玄宗所忌;建文若真出逃,亦只能隐姓埋名,终生不得露面。
他们失去的不仅是皇位,更是作为人的自由与尊严。
历史记载对废帝多持贬抑态度。
刘贺被称“荒淫”;李重茂几无评价;司马奕被记为“柔懦”;建文帝则被永乐朝史官描绘为“柔弱”“受奸臣蛊惑”。
这些评价,大多出自胜利者之手,或受当权者影响。
直到后世史家重新审视,才逐渐剥离污名,还原其身处结构中的无奈。
今日回看,废帝现象揭示了一个根本事实:在帝制中国,皇权并非绝对稳固。
它依赖于礼法、宗法、官僚体系、军事力量与舆论共识的多重支撑。
一旦这些支撑断裂,哪怕坐拥玉玺、身居九重,亦可一夕倾覆。
皇帝不是神,而是制度中的一环,当此环无法嵌合整体运转时,便会被替换——无论其本人是否愿意。

刘贺若稍知收敛,或可如汉宣帝般隐忍待机;李重茂若有母族强援,或能如唐文宗般发动甘露之变;司马奕若生在孝武帝时代,或不失为一守成之主;朱允炆若缓削藩、联宁王、固边防,或可逼朱棣不敢起兵。
但历史不容假设。
他们所处的时代、位置、对手与自身局限,共同织就了那张无法挣脱的网。
废帝之名,载于《本纪》之末,或附于他人传后;其事,散见于权臣列传、外戚世家、叛臣录中。
他们不是历史的主角,却是理解权力本质的关键切片。
从长安未央宫到建康台城,从建康宫阙到南京奉天殿,龙椅之下,白骨层层。
坐上去的人,未必能坐稳;被拽下来的人,未必真有罪。
这或许正是帝制最冷酷的真相。
史料对刘贺日常行为的记载,多来自霍光集团事后罗织。
但即便剔除夸大成分,其无视丧礼、滥授官爵、私带旧臣入宫等事,仍属严重违制。
汉代天子即位,需经“告庙”“谒高庙”“受玺”“朝群臣”等程序,象征与先帝、宗庙、百官的合法交接。
刘贺未完成仪式即行私事,等于未真正“继统”,霍光废之,反得“护礼”之名。

李重茂登基时,中宗灵柩尚在,国丧未除。
韦后急于立君,意在抢占法统先机。
但此举破坏“丧君不立”的古礼,为李隆基政变提供道德借口。
政变成功后,李旦以“中宗复辟,韦氏乱政”为由,否定李重茂继位合法性,称其“非正统所出”。
这种说法虽牵强,却有效切割了政变与弑君的界限。
司马奕被废诏书中,“嬖幸”一词极关键。
东晋士族极度重视门第与私德,君主若宠信低微之人,即被视为“失德”。
桓温利用此点,将政治废立包装为道德净化。
褚太后身为士族之女,对此深以为然,故甘为废帝工具。
这反映出门阀政治下,皇权连私人生活都不得自由。
建文削藩时,曾召朱棣入朝,朱棣称病不至。
后又削其护卫,激其反。

此为战略败笔。
若先调其离藩,再削兵权,或可不战而屈。
但建文君臣缺乏情报与决断,反使朱棣以“朝无奸臣,藩王自危”为由起兵,赢得部分宗室同情。
靖难之役初期,多地观望,正因建文朝廷举措失当。
废帝之后,新君往往大赦天下,以示“拨乱反正”。
霍光废刘贺后,立宣帝,大赦;李隆基废李重茂后,立睿宗,大赦;桓温废司马奕后,立简文帝,大赦;朱棣登基,亦大赦。
赦令内容多含“除苛法”“蠲赋税”,实为收买人心,巩固新政权合法性。
赦书本身,即是对前帝统治的否定。
被废之帝的封号,亦有讲究。
“废帝”为后世史家所加,当时称“海昏侯”“温王”“海西公”等,皆去帝号,降为臣爵。
此举意在从名分上彻底抹除其帝王身份,防止复辟或追思。

明代甚至销毁建文朝实录,严禁私藏建文文书,违者族诛。
这种记忆抹除,比肉体消灭更彻底。
然而,历史总有缝隙。
海昏侯墓出土《论语》《易经》简牍,证明刘贺受过良好教育,并非全然愚昧。
建文旧臣程济、史仲彬等传说护主逃亡,虽无确证,却反映民间对“正统”的执念。
司马奕后裔在南朝仍有记载,未被斩尽杀绝。
李重茂墓志近年出土,称其“温恭俭让”,或为后人追美,亦或真相被掩盖。
废帝现象,是帝制内在矛盾的爆发点。
它既证明皇权神圣不可侵犯,又证明皇权可被凡人废立。
这种悖论,贯穿两千年。
直到帝制终结,人们才真正意识到:龙椅之下,从来不是天命所归,而是无数人欲望、恐惧与算计的交汇之地。
被废之帝,不是历史的注脚配资开户,而是那交汇点上最刺眼的标记。
东方资本提示:文章来自网络,不代表本站观点。